党史专家金冲及:不只有“翻案”才是创新 -凯发k8官方旗舰厅

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照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金冲及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这次说是要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胡乔木、胡绳,才答应接受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金冲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叶群的卧室,旁边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处。访谈就在这样一个曾经的“历史现场”进行。
金冲及说他从高中时开始读胡绳的作品,并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书名,“那个时候没有能够实际跟着他学习,但事实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跟随胡乔木、胡绳工作,包括参与1990-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的编写。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官方党史之一,也是定义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依据。
先后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的胡乔木、胡绳曾就此做过多次重要的内部谈话,金冲及出于职业习惯对这些讲话都做了记录。他练过速记,又熟悉“二胡”的江苏口音,录下的内容极其详尽。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协助下将这些记录整理出版,定名为《一本书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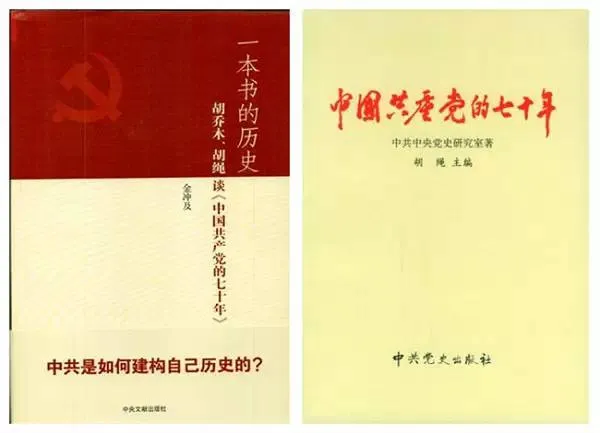
党史和党史的历史
谈胡乔木、胡绳
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确立党史叙述的关键人物

胡乔木(1912-1992),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图为胡乔木与毛泽东。
澎湃新闻:您长期跟着两位先生工作,也参与了《七十年》的编写,您觉得他们的讲话记录中,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冲及:比起具体的论点、问题,更要看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大家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看我后来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就会知道,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学的,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去做的。跟着他们工作,听他们那么多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有几点:第一,他们总是强调,写书要有一个笼罩全篇的思想、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国人过去写文章讲究“文气”,党史也要这么写,比如《七十年》要有贯穿党的70年历史的那么一口气,就是告诉别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第二,讲脉络线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几条。写《七十年》的时候胡绳同志讲过多次,40万字要写70年的复杂历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说明什么问题,详略得当。他不只一次提到《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但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上前线的故事那么长,几个字就了了。这一点从方法上来讲对我也一直有影响。乔木同志则是强调,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比如他讲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壮的历史,那你就应该用悲壮的文字写出来。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情,得有特写镜头。第三,强调“夹叙夹议”,乔木同志讲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带议论的。事实上他后来也说,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我们这里(中央文献研究室)写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们这个思想的影响。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泪。但巴金写到那里的时候如果突然跳出来说,你们看,这个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把你要议论的内容展示出来,这样议论就是画龙点睛。我感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他讲要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它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但要是一点议论都没有,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过讨论会上乔木同志也讲,希望同类著作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写法。第四,力求准确。他们很讲究文字干净。我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周恩来传》,给胡绳看过、改过。后来回忆的时候,胡绳说我都忘了,只记得给你勾(删)掉了几十个“了”字。他说我们讲历史都是过去时,一般不需要“了”。还有,写“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说“秘密”这两个字应删,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哪一次中央全会不是秘密召开的。所以他对文字、包括提法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胡绳(1918- 2000),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图为1991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绳与金冲及,摄于玉泉山。
谈党史研究
西安事变有些档案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
澎湃新闻:您觉得党史是一个政治理论还是一门科学?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金冲及:当然是科学。讲历史首先要有事实根据,你要有一个论点,得拿证据来。我和中宣部的领导同志也说过,宣传跟研究,是有联系、有差别的。宣传是把已经知道的结论——对或不对可以推敲——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已经解决的、有定论的问题。当然,宣传工作极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当然,我也很坦率地说,党史涉及的问题有时候敏感性很强。举个例子,西安事变。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说西安事变的事情你们不能随便写,因为张学良现在还在台湾,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1980年代初,我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的刊物《文献和研究》首次公开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几十个电报,那是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必要时,诛之为上。”我看过大量相关的(未公开)档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谓“必要时”是指两种情况,在另外的档案里讲得很具体——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进潼关,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种情况是内部不稳。在这些前提下“诛之为上”。这话本身没有错,周恩来也公开讲:只要你们中央军不进潼关,委员长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个话反过来意思就是,那要是进了潼关,对不起,他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但那个时候我把这封电报扣下了,没有公开。为什么呢?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必要时”指什么,看到这个就会简单说共产党是主张杀蒋介石的,这不符合实际。有些人就会渲染,说哦,原来还有一个“诛之为上”的说法。而且你越解释,人家越认为你要逃避问题。另一方面,张学良还在台湾,这不能不考虑。所以就没公开。后来有人编西安事变的书,把这个电报发了,万毅,当时的七大候补委员、东北军的将领,就写信给胡耀邦,说这个电报不该发。耀邦同志就通知这本书停售。那么我想,当时的决定没有错。所以,党史研究牵涉一些现实、敏感的问题,跟其他如古代史研究就不一样。我有一次看英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是根据美国1980年代初公布的档案写的。书里有好几个地方写到,公布的材料是复印的,有些地方被遮盖了。可见美国的档案,涉及到他认为有现实影响的、政治敏感的档案,也不会公布。但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出去的档案,大概比什么单位都多。这个话,我想大概并不夸张。

1992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右)与逄先知(中)、金冲及(左),摄于胡乔木寓所。
谈“非官方”党史
有些材料他们看不到,只能靠猜
澎湃新闻:您编著的可以说都是“官修”党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会上也非常活跃的党史学者?
金冲及: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华聊了半天。要说年龄,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门大学地下党,我是复旦大学地下党,所以讲经历很多事情都能够说到一起。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想这对人看待问题确实会有影响。高华的书出版后就寄给我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全部看,但我听别人说了大概印象。关于延安整风,他(高华)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延安整风核心的材料是会议记录,特别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等,很关键,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统地看过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他还是比较隔膜,很多是靠猜。2008年前后我到法国去,当时有一个德国教授讲毛泽东,我就说你有几件事讲得不对,我的根据有会议记录、有当时的电报,一条条讲。休息的时候他就过来,他说是啊,你讲的这些档案会议记录我们都看不到,只能去猜了。这倒也是老实话。延安整风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抢救运动。但是从会议记录来看,最中心的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实事求是也是这时提出来的。陈云也讲过一句话,说我延安整风时候把毛主席起草的这些电报文件系统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整风问题的报告(1941)
澎湃新闻: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杨奎松的东西我当然看,他书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书还是我给写的序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有许多长处,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说起来他们搞材料没有我们这样方便,有很多是一个省一个省的档案馆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里想问题。所以杨奎松到北大去当教授,我给他写的推荐信。推荐信当然都要全面地讲,我先讲了他的很多优点,也讲了一句,有时候有片面性。我觉得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结论没有错、但很笼统,你用大量的事实把它弄清楚。另一种是过去说错了,你纠正。现在都认为后面那种才是创新。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了一阵又流行短旗袍。(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这样讲,有的事情,有时候不方便讲我顶多不说,绝不会明知不是这样,却瞎写。假如是你的推测,用“看来、据我分析”,那也好。写过周恩来的高先生,他出国前我们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聊了一下午。我们都很熟。他的那部书,两头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编造的——但是,两段引文中间的叙说,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对这些情况,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怎么样的,就怎么说。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说,我绝不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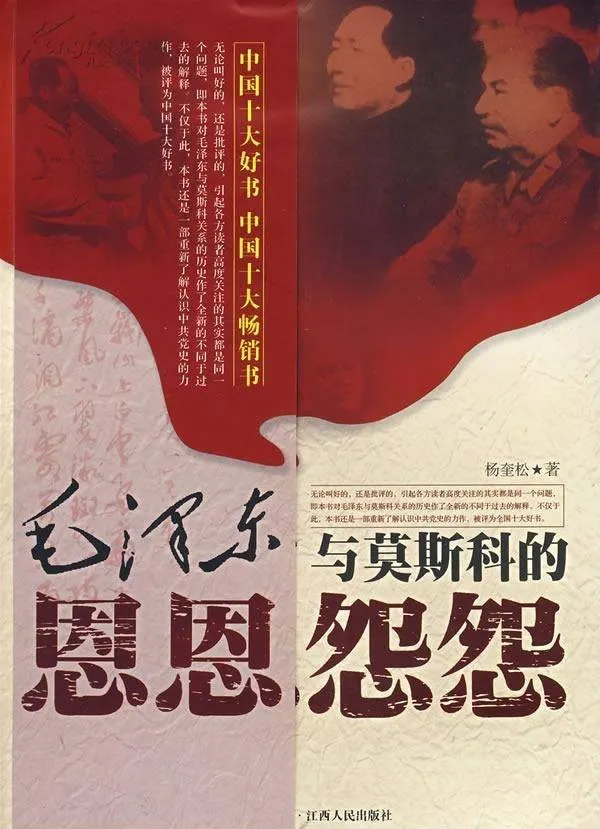
杨奎松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澎湃新闻:现在民间对中共党史、国民党史的研究都很有兴趣,他们可能更愿意听和官方叙述不一样的历史。您怎么看?
金冲及:可能有很多原因。现在的人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我说共产党对,他们就说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学家),你替政府辩护。另一个人说共产党不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挑它的过错讲,人们觉得这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就趋之若鹜)。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看问题是不是一定非得这样看?刚才说我和高华的父亲是同一辈人。我也在“文革”中吃过好几次苦啊,但现在我想的还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其实我这个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属于比较温和的,不是很极端的人。我当年上学也是去读书的,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革命。那时是想着,这国家搞到这样怎么办啊,大学生要改变它。那么共产党的主张我接受,我就参加。我现在不是说,国民党的好话一句也不能讲。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下长大的,我上学时就读过《缅甸荡寇志》(关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们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抗战)。但现在人好像有一种逆反心理,讲国民党净说好的,讲共产党净说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实啊。有些人说这些过去我都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只能说,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事实的一部分。现在人的心理状态就觉得,诶,这是老一套,那个新鲜,就相信那个。但是我看(有些研究),总是感觉,哎,他太年轻,他没有经历过。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没有义务去为什么辩护。我现在没有官职,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当然听不同的声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参加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三方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谈中日战争里的军事问题。日本、台湾学者的发言也给我很多启发,对于不同的叙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弃原来的看法。比如跟台湾学者蒋永敬讨论的时候,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一大也没有提。我仔细查材料,确实找不到,这话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讲,我接受这个意见,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蒋永敬说这他也能接受。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跟台湾学者可以达成共识: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没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实上是照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