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一省,为什么失速? -凯发k8官方旗舰厅
近日,各地公布了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在所有省份中,我国第一省广东的实际增速排名倒数前三。与此相对应的是江苏势头正劲。于是网上又开始热议:第一省要易主。今天聊聊广东为什么失速。

富广东,穷广东
广东的不平衡发展,可以说是这个经济第一大省长久以来的最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自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起,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与制造业成本优势,广东成为体系内外资本的最大受益者,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内陆地区的劳动力,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不过,这句话更准确的含义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珠三角”。
在大多数语境里,广东就是珠三角,珠三角就是广东。
这就是经济绝对优势携带的话语权对人下意识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不仅得益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还建立在复杂的财政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上。这种格局让广东的不平衡发展从珠三角向外延展。
作为广州的大后方,粤北在工业化初期曾扮演关键角色,但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由于发展条件和政策限制,这些区域逐渐边缘化。例如,河源和韶关因作为珠三角水源地,受到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限制,工业发展受阻,最终被定位为珠三角的“后花园”,发展潜力被封锁在较低水平。

相比之下,粤东和粤西地区拥有相对更多的资源与发展条件。如湛江的港口条件和平原,潮汕的特区地位和侨乡经济基础,但因政策倾斜和内陆连接不足,在中国加入wto后,珠三角凭借产业集群迅速发展,拉大了与粤东西北的经济差距。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广东实施“双转移”战略(2009-2015),试图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向粤东西北转移,但资本多流向江西、湖南等地,进一步压制了粤东西北的发展,使其沦为珠三角的经济腹地,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中的输家。
如今,整个非珠地区只占广东gdp约20%,差距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人均这块,非珠地区人均gdp比贵州省要低,倘若单独建省恐怕会在全国垫底。如果从深圳开车去湛江,经过广佛,肇庆,云浮,再到茂名,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途的风光,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到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穿过无数的山地隧道,最后抵达“菠萝的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缩影,更生动地诠释中心到边缘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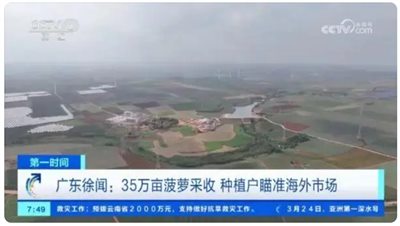
即便在珠三角内部,发展格局也十分不平衡,形成了明显的梯次。广深作为第一级梯次,靠着中心城市的金融和科技资源不断吸收利润,而佛山、东莞、惠州等作为“后厂”,则更多是制造业的附属。
中山这样的城市,虽然也曾有过辉煌的产业配套发展期,但近年来却难以突破,像是被封印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瓶颈中,逐渐在珠三角内部的竞争中掉队。江门和肇庆市区一样则沦为为大湾区的凑数的养老城市。
这种区域分化不仅是地理的分化,也体现在人群和阶层的分化中。珠三角的城市空间内部,随着资本的逐利与再生产,士绅化不断加剧,本地的土著居民与外地的打工人被逐渐排斥出核心的经济区域。

那些在cbd和新城建设中拆迁致富的周边村民成了新的食利阶层,他们往往身穿白汗衫、脚踩大拖鞋,却是城市的隐形富豪。而更多的“老广”,这些体制内的老员工,却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他们的子女也更容易沦为了服务业的无产阶级,日渐被新移民取代。
不可否认,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雁阵式”模式曾在产业发展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非珠三角地区承担能源供给、劳动力输出和第一产业保障角色,珠三角则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然而这一体系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尤其近两年,广东的经济增速已连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省内经济分布的不均衡,广东的财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三级财政的特性。广佛莞等城市在上缴省级和中央财政后,实际留存的资金相较于深圳以及江苏的同类城市显得有限,这使得它们在吸引新兴产业方面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
从非珠三角的角度看,广东到了后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帮扶在交通和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这些投入多为短期拉升gdp的重复建设,并未真正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尤其是粤东、粤西两个地区,以汕头和湛江为代表的城市在基建项目减少后,经济表现迅速下滑,名义上负增长。
一句话,广东整体经济发展正面临“头尾难顾”的局面,既要应对珠三角内部的资源争夺,又要处理长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下文具体探讨广东头部发动机部分出现什么问题。
中心问题:广东产业升级
广佛同沉
前三季度,所有万亿城市中,有两个城市增速垫底——这两个城市都在广东。熟悉这两座城市的人会知道,它们实际上关系紧密,几乎融为一体。广佛不仅建成区相连,而且主城区也直接接壤,佛山的禅桂与广州的荔湾已经连成一片,环城高速西段甚至穿越了佛山境内。倘若抛开行政区划来看,它们根本就是一座城市。它们的问题也很接近。

首先是佛山,今年经济拉垮的直接原因是外贸,在全国城市出口形势上半年整体尚可的情况下,佛山的出口却同比暴跌31%。这一状况主要受到欧美市场去库存和关税增加的影响,还有东南亚市场(如印尼)也针对佛山擅长的产业增加了关税(当然不排除由于广深跨境电商快速发展,货物由佛山企业生产,但以广深跨境电商企业的名义进行申报)。
从根本上来说,它的衰退与它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佛山的主导产业为房地产的周边,例如家具、家电、陶瓷、五金、门窗、涂料、灯饰、卫浴、塑管等,在大湾区许多房地产企业相继暴雷的情况下,这些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严重冲击。
广州经济近年来的失速可以总结为“地产危机”和“新能源”的双重冲击。过去支撑广州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日系车制造,如今都陷入了困境。
房地产原理等同于佛山——成也萧何败萧何,前几年恒大、碧桂园都是宇宙级别的房企,走哪都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而且这两城市跟房地产相关的配套产业也是全国独树一帜的,直接被一波房地产周期带走。
而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打乱了广州传统汽车制造的节奏。广州的汽车制造长期依赖丰田、本田等日系车企,然而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当下,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广州在这波转型中明显落后于深圳这样的城市,甚至不如重庆。新能源汽车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而广州在这一领域的产业布局显然落后。
从人文地理角度,广州是珠三角绝对的核心(但如果以资本投资流——边缘模型来看,核心是深圳,广州退居半边缘),广府的两个代表:广州 佛山,一个代表官商力量,一个代表珠三角本地民间商业的力量,共同组成了一个超级城市。
围绕广州-佛山地理核心,几乎等距离出现了肇庆、清远、东莞、江门、中山等城市,分别扼守西北东江进出珠三角的通道。珠三角平原拥有一个标准的中心城市-卫星城市构成的城镇体系。故而如果广州颓了,除了被深圳外溢的东莞以及特区珠海,其下面的肇庆、清远、中山、江门的经济增长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城中村
广东的城中村是一个相对独特的生产生活形态:城中村的房屋多由村民自行搭建,空间利用极尽紧凑。这里的生活充满了市井气息:狭窄的两边能握手的巷道、密集的民房、随处可见的招租广告和鳞次栉比的小商铺,构成了城市的“低端产业”栖息地。

这种形态不仅维系了大量打工者低廉的生活成本,也成为资本家压缩再生产成本的重要一环。租金低、生活便利、供应链完善,使得这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同打不散的泥鳅。广州的鞋服箱包批发市场、华南理工旁边的高教园区,腹地湖南湖北的劳动力,都在支撑这片土地上滚滚的商贸与制造业流动。
这种“村集体 产业集散”的形态虽然保留了强大的成本优势,却也带来了治理和规划的复杂性。
相比而言,以苏州、无锡、常州、宁波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其工业园区往往由县一级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布局整齐划一。工业园内部,曾经的自然村落被统一拆迁安置,这样的规划模式将地租与建筑收益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一种集中的土地金融体系。工业园区也注重环境配套,绿化整齐有序,园区内的大道两旁种满绿树,展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秩序感。

相对而言,珠三角地区以村集体为主体的土地收益模式则使得民房大量抢建,常常让人分不清哪是厂房哪是民房,形成了一个个像打乱的马赛克拼图般的自发秩序。
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佛山和东莞,由于基础设施投入较少,许多建设依赖村集体资金,使得地方政府整体负债率相对较低。这种村集体经济模式在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升级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导致低端产业难以退出历史舞台。
像顺德大力推进村级工业园拆迁改造,这种规模的调整起步较晚,与昆山、江阴等地相比已显落后,再加上巨额财政投入,不免让人感叹有亡羊补牢之感。由于过去十年缺乏前瞻性产业布局,使得珠三角(尤其西岸)在部分新兴领域的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例如,在新能源领域,常州已聚集了天合光能、蜂巢能源、中航锂电等行业龙头企业;无锡则培育了先导智能、微导、拉普拉斯、中鼎等半导体领军企业。相比之下,广东除深圳外,在新兴产业整体竞争力上显得相对薄弱。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多“嵌入型”特征。政府不仅依托产业园区和市级政策配套,还通过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扶持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强化政策导向。这种深度参与的体制模式显著提升了资源整合效率,推动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独角兽企业和隐形冠军。
同时,产业园区模式有效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发展。不过这种依赖产业园区的模式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托于“有为体制”,或体制参与的产业政策下的实体产业链。所以我们发现,苏南地区的主流富人群体往往是体制内资源的深度参与者。
深圳是广东未来吗?
深圳的成功是改开后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广东流传着一句话:“深圳是北京的,广州是广东的。”在广东人的印象中,深圳似乎更多是国家政策的试验之地,与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相比,深圳在文化、人口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虽然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一样,有着大量的城中村,但规划能力明显强不少,另外差异主要在于其经济体系中的制度设计。这使得深圳得以实现两次成功的产业升级,而这背后的深层逻辑也是对国家治理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刻映射。
作为计划单列市,享有超越一般副省级城市的权限,甚至被视为准直辖市,其财政收入没有多少经过广东省的分配,而是直达北京。这种财政自留权赋予深圳极高的财政独立性,使其可以以极高的效率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道路上不至于像东莞中山佛山那样像被轰炸过一样。
在税收和补贴方面,深圳也一直拥有全国领先的优惠政策,包括低税率、低社保费用,吸引了大批企业注册和运营。财政上的宽裕使得城市持续地投入公共建设和服务,从而增强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循环。
在第一次产业升级以后,深圳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这迫使它必须依赖于总部经济和高附加值产业。它需要吸引高利润的企业,把各地的利润通过关联业务流汇聚到深圳,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产业升级并非自然而然的经济演进,而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土地的紧缺、成本的高昂,让深圳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腾笼换鸟”,每一次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从最初的金融业外迁,到加工制造业的离去,深圳被迫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重心,这种调整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气”与政策的合力。

深圳对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吸纳是它“成功”的另一面。低社保与高房价的组合将深圳的劳动力流动性推到极限。深圳不是一个为多数人长期定居而设计的城市,而是一个又一个连绵的产业园,打工人像一排排干电池,安入撤出。深圳的大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写字楼和全国最多的公园,有限的住房供给与庞大的常住人口不成比例,表明深圳并不打算让所有人都长期留下。
深圳的产业升级的魔力仍不断吸引着年轻人源源而来。当然对于这些年轻人,定居并非现实选择,更多的是积累工作经验,随时准备去其他寻找更好的机会。讽刺的是,这是一种设计,却让人口的流动维持在一种最有利于城市效率的状态。
深圳凭借其低税率优势和高附加值产业,难免对大湾区其他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大量资本和人才涌入深圳,使得周边城市如广州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深圳的土地资源和成本难以支撑全产业链的覆盖,因此不得不依赖周边城市提供中低端制造与配套服务,电子信息产业的溢出效应也惠及了东莞和惠阳。
至于通过深中通道来带动中山和江门的发展,这仍需时间。尽管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带动了中山部分消费,但产业转移和带动作用仍然有限。从中山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4.5%,而深中通道开通后前三季度增速仅为4.1%这一点可以看出,深圳目前尚不足以显著拉动中山的经济增长,寄望深圳单核驱动整个大湾区发展也并不现实。
深圳高昂的房屋地块租售价格,企业在深圳注册经营的成本很高,目前还能被各种的优惠政策抵消。一旦没有了这些特殊政策的话,那么在深圳高昂的经营成本,会让很多企业搬走——去到长三角或者周边城市。所以,深圳目前只能不断地向上面维持和索要特殊优惠政策。
未来走向
可以预见,广东的未来发展将是在一系列内在矛盾中艰难前行,而这些矛盾将决定广东能否有效化解发展危机,扭转与江苏省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被超越。
一个是廉价民生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广州是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广州吃的方面物美价廉、丰俭由人,衣服、箱包、花卉、帽子、饰品、零食是全省批发中心。衣食租行,都比省内各地市成本低。城中村一方面维持了小商贸的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难题。
另一个是地理不平衡的矛盾。广东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继续面对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平衡带来的矛盾在财政分配和区域资源倾斜中显得尤为突出。未来,广东需要在继续巩固珠三角作为经济核心地位的同时,找到有效的策略来激发非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
笔者之前写过一篇关于粤东、粤西的《广东发展启示录》,最后再说几点:
本地收租的食利阶层秉持着“不影响收租喝茶就行”的观念,不过现在就没得喝了。老广收租的主力的城中村,租客主要是批发市场带动的产业链的打工群体。现在私营小工厂不景气,从大沙头到罗冲围,都不好收租了。
房地产低迷不振,广本和广丰这些合资厂能带动的产业链也相对单薄,不如国产供应链那样丰富广泛。广州未来的发展,需要从新兴领域如扶持小鹏汽车和探索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中找到突破口。事实上小鹏下半年效益还不错,如果小鹏汽车能更上一层楼,与之关联的区域,尤其是作为生产基地的卫星城肇庆,也将随之受益。

而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正经历的转型期注定是痛苦的,就像几年前的东莞一样,它们需要放弃过去以房地产及低附加值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目前来看只有北滘是最有希望在智能制造上突破的)。而这种转型至少需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难听的话就是,高精尖的新兴产业都已经被京沪深杭渝分完了,其他广东城市只能通过产业配套和承接他们高端产业的部分外溢环节,目前看来能承接到的只能是深圳。
但深圳自身也不明朗,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碰撞的力度必然加大,深圳的领先领域新能源、生物技术、无人机、信息通信、智能制造……几乎每个领域都将可能面临打压。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区域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