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 -凯发k8官方旗舰厅
随着共和党确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许多人畅想的特朗普完全执政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这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政治现实仍需观察,共和党在众议院内部的优势极为微弱,这将极端放大不安分议员的个人声音。共和党前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黯然下台是一个例证。
不过,上述事实不会改变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拥有更大自由的现实。媒体对特朗普人事任命的高度关注暗示了美国人对下一届政府可能举措的巨大兴趣。特朗普将黑莉和蓬佩奥踢出局,以及任命马斯克和拉玛斯瓦米为政府效率部门(doge)负责人都迅速成为新闻头版,这波人事舆论热潮将一直维持到特朗普正式上台。

笔者无意为特朗普各部门人选做出任何预测,毕竟前几天媒体疯传蓬佩奥担任防长的流言已经被名不见经传的前步兵上尉皮特·赫格赛斯所代替。反对派将这一任命视为特朗普无人可用或者缺乏政治经验的结果;支持者则将华尔街日报刚刚提及的退伍军人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将任命视为特朗普全面改革军方高层将领任命的一部分。
考虑到蓬佩奥和赫格赛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两极态度,这将加深乌克兰人的幻灭感。盖茨的司法部长任命和图尔西的国家情报总监任命,更是让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博尔顿破口大骂。
南辕北辙的预测说明一个事实,除了特朗普真正的核心幕僚之外,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预测与一般大众在人事任命上的揣测没有本质区别。预测确实是喧嚣的热点,但笔者更关注的是,特朗普一系列人事任命背后究竟代表何种政治观念或者政治结构的变化。从特朗普现有的人事任命趋势看,展望未来四年,今年可能是对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而言最好的一年。

在我们前几天的文章《特朗普的归来,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复辟”》中,我们说到二周目的特朗普不只属于保守主义,全球化本身的重构、演变,自反矛盾和自我修复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变化,让各国和曾经作为全球化引领者的美国同样,共同走入了一个本土主义叙事的生长期。
当时文章限于篇幅,并没有详细展开美国政坛中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纠葛和区别。以全球和本土的结构性对立为视角是理解特朗普二次当选的重要方式。但这种视角可能需要进一步阐释为何在当下这个周期以特朗普运动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比新保守/新自由主义和左翼运动更能代表本土意识的问题,这与传统保守主义对本土意识的强烈偏好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特朗普的二次上台是传统保守主义毋庸置疑的复兴。在传统保守主义复兴的背后,是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化。
以任命更多的非建制派圈外人和组建政府效率部门为标志,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加速两党政治基本盘的重塑,以反觉醒为重点的文化议程将成为接下来舆论交锋的重点。传统保守主义向新保守/新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的总复仇正式拉开帷幕。
特朗普的传统保守主义血统
当代美国学术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六七十年代后美国智识阶层的许多人有一个有趣的论断,即美国没有保守主义传统。这一论断最终可以收束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没有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没有需要保存的旧制度。
在这一意义上,即便美国拥有保守主义,也是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保守主义——一种拥护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用亨廷顿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洛克式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由主义者指出了保守主义的长期困境。保守主义在智识上缺乏像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样清晰明确的谱系。它似乎更偏好天才人物的创造性发挥。不过,如果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将美国的保守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附庸只能成为一叶障目。
以特朗普的核心政策为例,他的政策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在文化领域高度强调文化战争的重要性,积极捍卫以传统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方式;在经济领域再反对政府权力过分渗透的同时,强调社会团结的重要性,照顾工人和乡村阶层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强调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倾向采用高额关税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不干涉主义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

特朗普的各项政策与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主流秩序格格不入。但一旦进入到自由主义者所不熟悉的传统保守主义路径中,我们将立刻能够发现这些政策在正统的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具有强烈的一致性。
上一个与特朗普基本政策高度一致的人,是帕特·布坎南。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强调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传统保守主义的灾难性破坏。这不仅体现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也体现在文化冲突上,最重要的是对美国的未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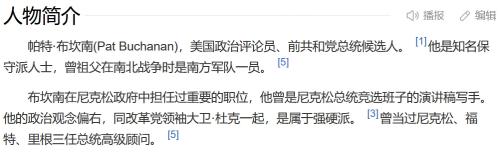
他指责共和党建制派与民主党一起屈服资本主义下的抽象原子化个人,向经济主义投降。这种投降的结果是“有一大群孩子的年轻夫妇家庭现在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只有富裕的年轻人才能负担得起那种‘生活方式’,而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在一个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试图代表传统保守主义与老布什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正是他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文化战争这一概念正式推入美国的政治漩涡中。
再上一个与特朗普政策基本一致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是罗斯福新政联盟的长期对手,罗伯特·塔夫脱。作为共和党参议院的长期领导者,他组建了一个包含共和民主两党在内的保守派联盟。他支持保障工人权利,又反对国家权力的过分侵入。他对底层民众的支持突出表现他对《住房法案》的支持上。


不干涉主义可能是他最为著名的态度。他反对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反对美国加入联合国,他同时也反对北约,并质疑美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合宪性。与小塔夫脱的不干涉主义相比,特朗普的退群主张即便不是一脉相承,也只能说比较温和。
二战后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拉塞尔·柯克评价认为,塔夫脱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真正品格和气质。他在其所撰写的《罗伯特·a·塔夫脱的政治原则》中一书写道,“在‘世界大同’的空洞言辞已无法再引人发笑之后,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审慎维护和平的努力以及摒弃帝国主义的宏伟方略,依旧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这一谱系当然可以进一步往前追溯,并在追溯中让我们发现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正统的保守主义路线中的重要性。对一般读者而言,笔者认为这种政策和理念的连续性追溯已经充分说明了特朗普继承了一个确实存在保守主义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布坎南和小塔夫脱的政治实践中,也体现在拉塞尔·柯克和保罗·戈德弗里德这样真正的保守主义大脑中。
或者更准确地说,今日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将特朗普视为难以理解的异类,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地将美国传统保守主义视之不见。在这种路径下,他们只能得出一个单项维度的结论,即特朗普运动仅仅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的反抗。
什么是传统保守主义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看,特朗普运动是美国本土意识对新自由主义普世秩序的反抗。甚至特朗普本人是否是一个坚定的传统保守主义者都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正如笔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是在2010年后才最终确认自己的共和党身份。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否定特朗普胜选与传统保守主义复兴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什么是传统保守主义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
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全面梳理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议题。这不妨碍笔者有针对性的指出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一言以蔽之,传统保守主义的全部主张都可以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展开,即个人因为共同体而存在。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古老谏言,“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人类拥有一个生物学的大脑可以进行独立思维,但我们称之为人的东西只能在共同体中产生。
举一个不那么精确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每分钟的心跳多少,甚至他的基因序列是什么。但对我们而言,一个活生生的人指的是他与我们,或者说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仇敌,他可以是亲人也可以是陌生人,但只有在我与他人的交互中,人这个概念才能产生意义。
对保守主义者而言,这意味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即人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之中。近代社会契约论所幻想的抽象原子化个体既不具有历史性,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逻辑前提。
在共同体本位的思考模式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个人自由问题上的混淆才能辩清。作为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自由主义者经常宣称由于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也接受个人自由的观念,所以它们即便不是自由主义的,也是被自由主义化的。显然这是没有搞清楚两种自由间的本质区别。
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个人自由是一种基于抽象化原子个体下的普遍自由。在抽出一切特殊性要素后,他们获得了一个只能在观念中成立的人的空集,并反过来作为一切平等权利的基础。这种对个人意志的讨好产生了一种逻辑结果,即个人意志的至高无上性,共同体成为了个人意志的附属品,为个人意志服务。
对传统保守主义而言,个人自由不是抽象理念的结果,而是每个地区不同历史文化习俗的结果。用伯克的话说,法国人的自由不是英国人的自由。不存在一个普世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只存在于由各个共同体所塑造的具体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是有限度的,也符合共同体的内部共识。换而言之,个人自由从属共同体规范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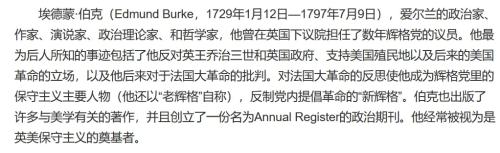
这种澄清也同样适用许多其他的混淆。比如许多人经常将保守主义与自由放任的亲商业政策以及小政府联系起来。不得不说,这种刻板印象荼毒之广充分说明了当代保守主义在宣传能力上的弱势。
伯克在奠定保守主义基本原则时,的确强调过自由市场的价值。亚当·斯密更是凭借伯克密友的关系,强调伯克支持他的主张。但伯克自由市场依旧以良性的共同体为前提,只有在共同体内部对基本的商业交换形成有效共识的情况下,自由市场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将经常上演。
这也是为何伯克会特别注重小农场主稳定性的价值。从纯粹的资本角度看,以农场主和小制造业主为主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跨国或者垄断资本的侵入。用伯克自己的话说,“至于较弱的资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只要犯了什么小错误,它们就会进一步削弱、衰弱、丧失生产力,甚至可能完全毁灭。”但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捍卫这些在资本上无利可图的阶层,他们是维系地方共同体良性运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伯克的这种想法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传统保守主义对小政府偏好的真正想法。需要强调的是,传统保守主义重来没有将自己与小政府或者大政府这样的目标明确绑定,英美传统保守主义和欧陆传统保守主义在这一点的偏好上就有明显的不同。甚至伯克本人也强调过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接受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
英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偏好更多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即如无必要,不加改变。比如,在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个社区中,大家已经构建出一整套长期稳定的生活方式,社区内部的成员也不存在真正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传统保守主义认为政府不需要再额外指手画脚;强大的外力侵入反而可能摧毁原有社区共同体的和谐。

甚至传统保守主义对觉醒运动的反抗也是基于这种理念。文化觉醒运动已经威胁到共同体自身的和谐和团结,一个丧失了和谐与团结的共同体也就无法在为政治活动提供稳定和共识。没有这种稳定和共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是空中楼阁,在无数个人意志强烈的冲突中,人类社会终将迎来自己的穷途末日。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结论,不难发现传统保守主义就是特朗普路线的精神实质。他对工人阶层的重视,试图减轻农场主和小制造业主的负担,以及不干涉主义政策都是传统保守主义修复美国共同体的尝试。
特朗普运动的标志性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传统保守主义直接的意象化。它从表面看,是一种对美好岁月的怀旧。但这种怀旧是为了修复共同体内部撕裂的精神坐标,让美国民众再次想象起一个团结的美利坚。

这也是传统保守主义和本土意识之间天然一致性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愿景之下,保守主义对本土意识有着明显的偏好。这不仅体现在对地方社区共同体的偏好上,也体现在对民族或者国家共同体的偏好上。它从根本上反对理性主义的普世政治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确定,特朗普运动是本土意识的复兴,同时也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
别子为宗的新保守主义
在对传统保守主义完成粗略解释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即新保守主义究竟是不是保守主义。
笔者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部分的历史回顾是一个更合适的切入口。敏锐的读者已经发现,从1953年小塔夫脱去世,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胜选,传统保守主义似乎存在巨大的空缺。似乎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传统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偃旗息鼓了数十年。或者更准确的说,布坎南的失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近数十年的传统保守主义一直处于低谷之中。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理解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杂关系的准确抓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以种族平等为核心,进步派大力推动所谓的平权运动。黑人政治权利的扩张是标志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对美国南方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剧烈影响。与南北内战一样,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南方政治成为道德和政治上的批判目标。用南方保守派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扬基人对迪克西人的再次胜利。

南方保守主义的衰弱导致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小塔夫脱在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建立的保守派多数联盟濒临崩溃,进步联盟获得了从最高法院到总统再到国会的多数。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寻找新的力量,或者说新的竞选联盟成为传统保守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保守主义粉墨登场了。
对当时的传统保守主义者而言,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保守主义至少在两个核心观点上符合传统保守主义的想法。其一是对个人自由的强烈偏好;其二是坚定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入侵。
与里根时代的冷战情况不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更多扮演意识形态输出的一方。美国则因为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深陷泥潭之中。传统保守主义者将这种情况视为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衰弱的表现。新保守主义对上述核心观点的态度正好满足捍卫传统美国生活方式的想法。从智识上看,几乎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出自知识阶层,尤其是犹太知识阶层。传统保守主义也将新保守主义视为自己扩大在智识阶层影响力的机会。
正是传统保守主义者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为新保守主义打开大门。拉塞尔·柯克也只是充其量认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过于关注在电视上获取影响力,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急躁罢了。然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策略成功了。他们成功利用电视这一载体夺取了保守主义内部的话语权,接下来他们更是将传统保守主义逐渐从保守派杂志和智库中清除出去。
这种清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传统保守主义完全从学术界和政治界消失了一样。尤其是在冷战的意外胜利后,对个人自由的偏好变成了对个人权利的狂热信仰,对苏联的反抗变成了对美国普世制度的优越性。以至于柯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终于幡然悔悟,发现自己成为孤立的少数派。新保守主义也塑造了今日保守主义刻板印象的合集。强烈的对外干涉偏好和亲富豪阶层的国内态度成为其中标志性的态度。

事后看,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显然对新保守主义产生了误判。或者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忽视了新保守主义的血统问题。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几乎都是带有犹太血统左翼自由主义乃至前托派成员。
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就在其自传性质的思想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正是冷战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让他成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这批新保守主义者相信,今日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美国已经陷入到一场新的永恒战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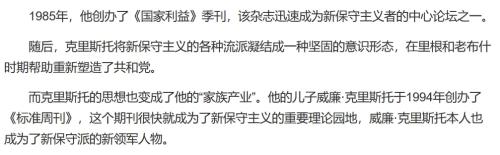
美苏冷战的结束只是另一场冷战的开始。“它是一种同时针对政治和社会集体主义,以及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不会赢,但它会让我们都成为失败者。我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美国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既然另一场‘冷战’已经结束,真正的冷战已经开始。”
任何对托派学说有所了解的读者很容易其看出克里斯托思想中挥之不去的影子。或者更明确地说,这种永恒的冷战与不断革命论之间分享有同一张精神实质。这最终催生出新保守主义强烈的对外干涉愿望。苏联的瓦解不是终点,必须要将美国的制度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克里斯托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看上去摆脱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曾经他们所认同的观念结构早已内嵌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去。这正是柯克那代传统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他们太过急迫地吸收新鲜血液,以至于忘记真正促使新保守主义诞生的思想动机更多来自于前托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能反感。
这种反感甚至可以追溯到克里斯托在学生时期托派和斯派在会议室中的宗派主义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地位上的特权,而不是恶运强加给我们的负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谴责任何人或任何事是‘精英主义’。精英就是我们——被历史选中的‘少数幸福的人’,引导我们的同胞走向世俗的救赎。”
这种与传统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精神气质本应在一开始就被发现,传统保守主义者也最终用自己几十年的低潮为这种错误买单。布坎南时运不济的尝试以及不那么充分的克里斯玛早已暗示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未来——静待时机,静待领袖。
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
特朗普崛起与08年经济危机或者说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关系,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详述过,不再累述。传统保守主义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克里斯玛领袖。通过与新保守主义或者说共和党建制派的全面斗争,传统保守主义再次夺回了自己的声音。
这也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的决定性不同。这不是单纯两党间在四年内的轮换,而是传统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格局的全面清算。这也是为何大量两党人士会出现互换基本盘的原因。他们是深层次政治重组的结构性祭品。切尼更是从共和党众议院曾经的第三号人物沦落到只能为哈里斯辅助竞选。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初期人事任命进一步显示出清算的动向。这种动向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对新保守主义者的大量出局。
博尔顿和切尼这样在第一任期就与特朗普闹翻的铁杆新保守主义者最先出局。其次是黑莉这样号称的温和派代表。自初选结束之后,在本次大选的最后时刻,特朗普都在暗地里拒绝了黑莉的辅选。最后则是像蓬佩奥这样的投机人物。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曾经都是被称为共和党建制派的一部分。特朗普在胜选之后更是直接将黑莉和蓬佩奥踢出局,断绝了舆论揣测的念想。
或许有人会提及卢比奥这样潜在的国务卿人选。茶党出身的卢比奥不能算得上是标准的共和党建制派,但最为关键的是他的转向能力。作为一个在2022年还高喊支持乌克兰的人,在2024年利用自己的参议员身份对援乌法案投下反对票。究竟是谁导致他态度出现180度转变,答案不言而喻。
约翰·图恩确实算得上建制派,但为了获得特朗普对他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支持,早在今年3月就直奔海湖庄园试图缓和关系。这种游说的结果避免了特朗普公开对特定候选人的支持。在昨晚的投票结束之后,图恩更是迅速宣称,“这个共和党团队团结一致,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议程,我们的工作从今天开始”。

第二是对华盛顿官僚系统的全面清洗上。新防长的任命是典型表现。特朗普绝非无人可用,他的目的就在于削弱军方高层的影响力。在这一目的的趋势下,任命前步兵上尉担任防长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退伍军人委员会(尚未最终确定名字,也可能叫战士委员会)才是更致命的杀手锏。这意味特朗普有能力通过行政命令创造出针对高级军官的人事考核制度,迫使他们服从特朗普运动的意志。

马特·盖茨被提名为司法部长更是对司法部赤裸裸的威胁。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盖茨的特点就在于其毫不妥协的作风,以至于在党内都是刺头一般的存在。在共和党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的情况下,盖茨被提名为司法部长堪称一举三赢。这有利于约翰逊议长管理众议院,也满足特朗普对司法部全面清洗的诉求,盖茨本人也有了更大的舞台,为日后竞选参议员积累资本。

特朗普清洗华盛顿官僚系统的原因与机构自身的党派倾向密切相关。如果说深蓝州的民主党能够领先共和党20-30个百分点,那么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率,能够达到令人震惊的1比8甚至1比9。在今年的选举中,哈里斯就以90.2%的支持率遥遥领先特朗普的6.5%。由于华盛顿特区的特殊性质,大部分选民都与官僚机构密切相关。
这种极度扭曲的数据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僚机构,至少中央官僚机构有明确的党派倾向。特朗普倾向在官僚系统之外挑选候选人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证明,党派倾向严重的官僚部门既不能与特朗普关系融洽,也不能有效执行传统保守主义真正想要推行的议程。
可以预见的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传统保守主义将会加大对包括lgbt和dei在内的觉醒议程进一步攻击,并直接向教师工会和公务员工会这样支持这一议程的铁杆民主党群体开战。近年来兴起的家长权利运动只是风暴来临前的先声。



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也符合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诉求,即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官僚机构进行系统性削减。清除官僚主义,提升政府效率更多是为了满足马斯克这样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胃口。或者说,这是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策略性联盟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为了避免主题过分松散,笔者在此只简单总结,在进步自由主义全面占据主流机构话语权的情况下,两者拥有共同的结盟基础和相似的关键主张。这一次传统保守主义没有碰到上次与新保守主义结盟的窘迫。对人员更为稀少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传统保守主义才是他们需要攀附的对象。
不过从政治现实看,这种效率提升必然会带有明显的偏好性,环境局、大学、公立学校这类非常亲民主党的机构都可能是优先清算的对象。
对共和党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特朗普,而是究竟谁能继承特朗普创造的竞选联盟。特朗普的成功与他超强的领袖魅力密切相关,但重新由传统保守主义掌控的共和党需要找到能够将新的竞选联盟稳固下来的办法。万斯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但唯有时间才能清楚告诉我们一切。
